版权声明: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,作为参考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,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,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!转载本站内容,请注明转载网址、作者和出处,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。
作者:佚名 来源于:中华书画网
钱锺书对中国书画史论的贡献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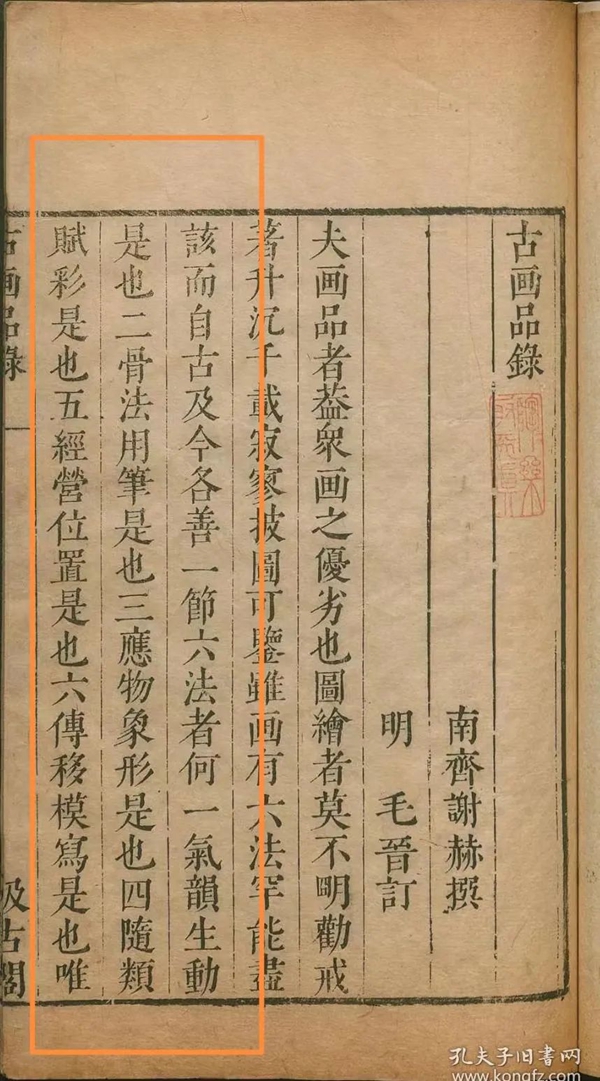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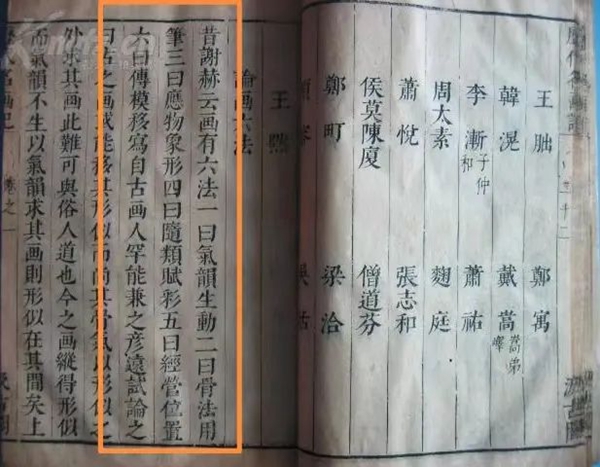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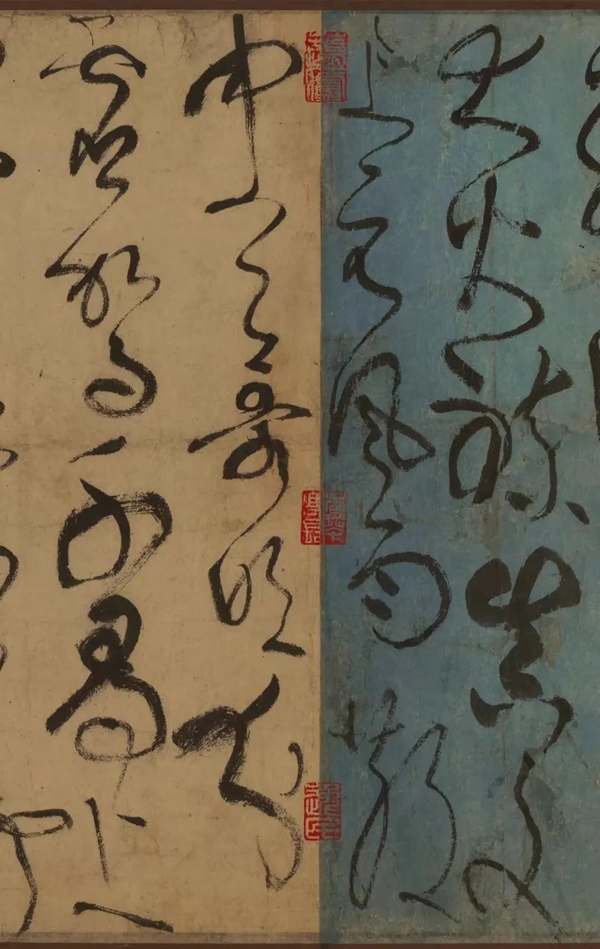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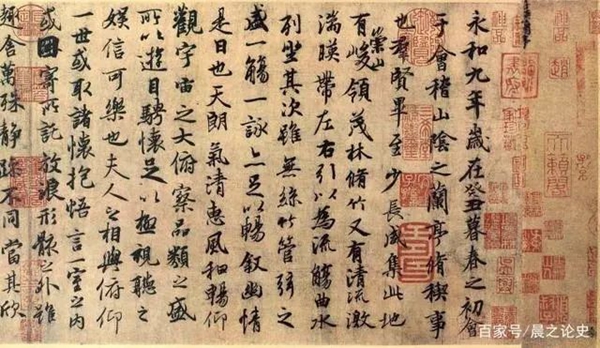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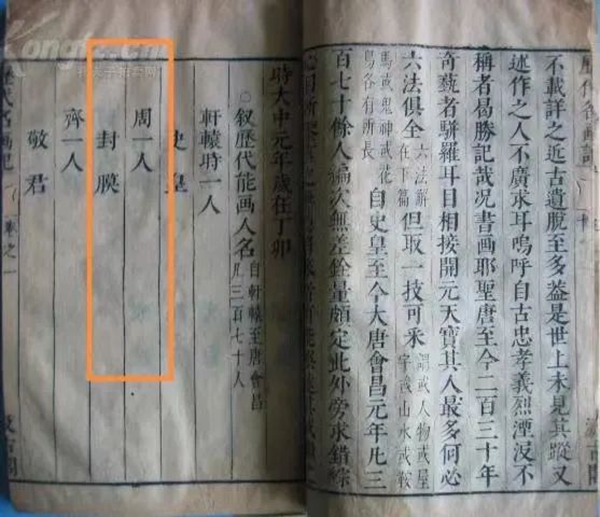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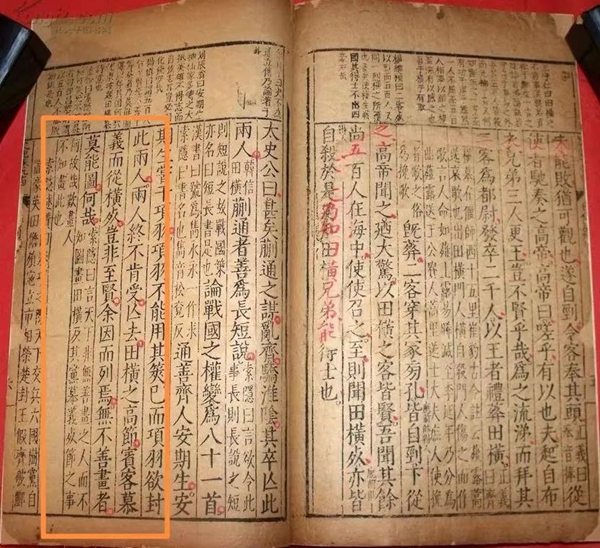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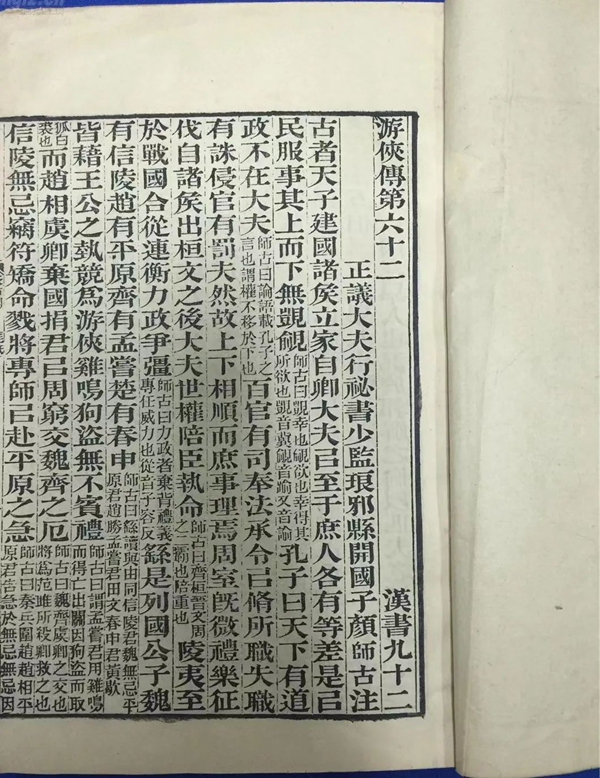


上一篇: 古代文学鉴赏的传统方式
下一篇: 《石渠宝笈》印章钤盖有讲究
标签:
【相关文章】
版权声明: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,作为参考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,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,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!转载本站内容,请注明转载网址、作者和出处,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。
Copyright ©cqwhw.cn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 | 中国瓷器网(中国瓷器文化网) 版权所有

